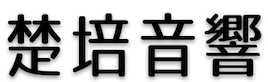文/明格斯
朝聖者但丁在《神曲》的最初,生命的中途,前不見路,遇到不下於死亡之恐懼的黑森林,出現了三頭猛獸擋住去路。約莫五歲左右,我自己一個人,從家裡繞到打彈珠的砂地之前,每必面對大戶人家不懷好意狂吠的家犬,再穿過髒污的大排水溝上的簡陋木橋。一番驚懼後,踩到砂地第一步的踏實快樂。我覺得在Beethoven 第四或第九號交響曲第一樂章前段「從黑暗到光明」,應該浮現類似的畫面。
無論你喜不喜歡Beethoven的二元辯證推演,這是他奏鳴曲式的魔法的賣點與戲法(shtick)。
Beethoven 的交響曲,充滿等待綿延的哲學,以及黑格爾辯證的思維。因為調性、半音使用與黑暗下曖昧不明的等待,前後對照下,讓光更加顯得明亮、來臨時更令人興奮。
Chailly 的戲劇原則,並不遵守這樣的雄辯理路。在速度感、平整力道的驅使下,你像是被父親重複拋上空中的小孩,腎上腺素飆高不止。在離心力的飛輪運動下,路的起伏其實不大,也沒有山谷溝渠,腳下的波濤雖洶湧不止,但絕非吞噬心靈的暗流黑潮,你隨著渦輪的 perpetuum mobile 無窮搖擺,興奮異常,但沒有一件旅途中經歷的事件,在你的內臟肉身,劃下過深的刻痕。
這聽來像是深切的指責。我在別處提過,對此全集感到的遺憾是:Beethoven 的交響曲,真的像Chailly 渦輪引擎驅進下,毫無遲疑,毫無停滯,毫不示弱,毫無 Faustian striving,全是正面加法之光?
( 心中的O.S.: 後來被Bruckner 在第五號翻轉過的手法, 九號 “Ode to Joy" 最後樂章:「一一登場的各樂章主題,各各被否定掉,被新的主題與自由的新聲所取代」。這塊構曲「橡皮擦」的草擬、拭去與掙扎,確立之前所應嘗試耗盡的種種options 的精神,我覺得應該是Beethoven的all too human 之「非強者、而是反覆探索之人」一個重要面向。)
偶數交響曲的平反,是Chailly 的一樁成就。其中動過大刀的動容風景,又以四號、六號與八號最為突出。這些補過紅肉、健身過的交響曲,不再是小家碧玉的安份淑女,微風怡人的華爾特式大自然,或是復古的海頓(CPE ?) 戲謔,而都變成了運動神經發達,動作敏捷的輕筋肉體操男。
與此相對的一極,較有問題的是,「最Beethoven」、最為明暗戲劇對立、最多掙扎糾結的以下幾首:三號,五號,與九號。( 動作場面細膩編舞過的鋼鐵人,如何演好內心戲,或至少展現出放肆的粗暴猛勇呢?)
在Chailly的眼光下,九首交響曲應該是巨人肉身一體的opus magnum,同時各自從毛孔血管裡揮汗呼納、互通氣息的。我覺得,整個實驗的核心價值,在一道貫之的作品引出的光明與生之喜悅,以及毫不壓抑的意志貫徹,不容置疑,這是對於affirmative joy 的長篇頌歌。此外,以Chailly 再三強調的「九曲一貫之」的 integral approach,抑強拉弱,縮小曲子之間的差距,也縮小樂章的劇烈起伏(trio 的部份,一律不附予一個綠洲般的停頓感)。雄雌、強弱、明暗、聲部、樂器色彩上的種種對立,在此 vision 更高指導原則下,必須被消弭或是抹平。幸運的是,Chailly 的萊比錫樂團,是極極少數可以完整實踐這樣特色與要求的超技團體。
光就這一點,Chailly 的Beethoven 全集的 vision 與成就即可確立,也跨過了另一個世代,立下典範。Rattle, Abbado, Pletnev, Thielemann,向前腳步遲疑,與old school 糾葛不清,在Beethoven的新世紀意義上,都功虧一簣,未能上陸搶灘。
史詩已死,神話的monumental approach只會使人發笑,或哈欠連連。
在去除Beethoven 的薛西佛斯與普羅米修斯的交響神格化前提下,Chailly 與萊比錫布商管弦樂團的大破大立、膽識、超技下仍固如金湯的肌理層次、以及意志的徹底一致,都樹立一個新世紀重要的里程碑。即使,前面提到對於這部百害不侵「鋼鐵人」之Beethoven 形象的疑惑,仍揮之不去。
古樂的「去浪漫張力」( 目前最讓我信服的是Bruggen),到目前為止,只捕捉了Beethoven的另一個面向。在去神聖化的當代情境下,天才的悲劇精神,浮士德之掙扎皆可拋去,那取而代之的是何種面貌呢?Chailly 的答案似乎還不夠完整,革命尚未成功,但他的影響,跟他殺出的一條血路,將是未來可以積極開拓的一條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