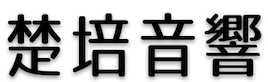溫度是有聲音的,譬如說,冷。
旅德頭一年的棲身之處是個地下室,與地面有著一小段距離的氣窗面對的是房子的後花園,除了白天上班時間的一點聲音,以及不遠處輕軌電車行駛的低頻振動外,只要不開窗,室內靜得令人耳鳴。知道日出日落卻又像與世隔絕的狀態如同處於陰陽交界,令人發慌,於是除非下雪,否則我都盡量讓窗戶開點縫,使聲音流進來。從花園後街行人的對話、衣物摩擦、腳步聲、小鳥啼叫、松鼠穿梭、昆蟲拍動翅膀,再到果實墜落、葉子與花瓣滾動於草皮上等,漸漸地發現原來春夏秋冬都有各自的音色。最可愛的是雪花,當很靜很靜的時候,你會聽見那白靄靄的一片,時不時發出非常細微,類似水晶杯破裂的高頻聲,活像是精靈耳語。
冷,對斯堪地半島的居民而言也就是個日常,尤其是佈滿冰川的挪威。不知是這樣的水土所養成的人民特有的,或是其他什麼因素,總之,許多挪威音樂家的作品或演出,經常性地會帶著某種極具辨識度的冷調,即使聽來熱鬧的舞曲中,依然有涼風穿梭。該說這是他們面對人生的態度吧,一種不疾不徐,即使悲傷,即使好友過世了,會跳支舞、唱幾首歌送別,然後繼續往前走的態度。
「急奔難免跌跤,緩一點就行了,來唱唱歌吧。」小提琴輕輕動了幾下,口簧響起來,我聽到他們這麼說著。心裡的躁火消散,閉上眼彷彿又見到那白靄靄的一片,而遠方太陽正逐漸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