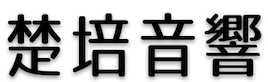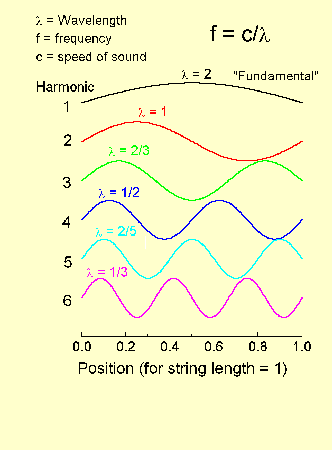文/傑拉德
熱心音響的人很自然地會蒐集屬於自己的音樂。可能,這些音樂的數量不大;也可能,遭致某些愛樂者物議。
我是想得開,承認自己喜歡的是聲音,並沒有什麼難為情的。我喜歡良好音響播放出來的「聲音」,想像它、幫它編個故事,相信這樂趣並不下於聽「音樂」。有時候我還覺得,我的想像力比單純的愛樂者更好呢,當這些神妙的時刻來臨時,我想,我聽到的應該就是音樂家的私語了。
回想起自己一路以新台幣與音響獸拼搏過來,除了一身血、滿口胡說八道的音響經之外,對聲音的深一層認識應是最大收穫。容我試著簡單地將這荒唐寫下。
「AR 3a」
1994 年發生的事。一個很好的同學自遠地來,要我陪他按圖索驥,尋新千里馬 AR 3a 去。
乖乖,我一聽到 AR 3a 播放的鋼琴聲,二話不說立刻墊了一個多月的窮薪資進去‧‧‧
那便開始了我無止盡的音響玩物興。
當時身邊只有一部 6L6 Push-Pull 管機和一組喇叭線,我每天下班後都把時間全耗在 3/5 A 與 AR 3a 喇叭線更換、擺位移動之間。
AR 3a 似乎從來都沒有發出真正驚豔的聲音,糊糊的自前方兩米處不住地丟音樂糊塊給我,可當時我竟沒有能力去改善它。
一天,一個同學來我家,試放了一張很難聽的 CD,鋼琴家 Richter 彈奏的舒伯特。那是一種很開玩笑的錄音水平,坦白說,我當時很不以為然這類歷史現場記錄,「可能只是給在乎音樂的人聽的吧?」我心下暗自嘀咕「 癡人。」
我有點不高興,話裡帶刺地責問他「為什麼要花錢在這種料上頭?」把鋼琴家、錄音兩損哩。我那羞赧內向的同學顯然很不好意思,整個晚上都在試圖解釋他也是依專業音樂雜誌評鑑購買的啊。
這個 Richter 頗讓我對同學的品味起了疑問。
「我在 AR 3a 上停留了一段長時間。」
一來確是因為阮囊羞澀,再來也因為花了一些心思在音樂軟體上。
「音響是手段,音樂才是目的」這句銘言,現在是頗不以為然,但在當時卻不敢不奉為圭臬。我買了幾本介紹古典音樂的導聆書、CD 指南,就此按圖索驥、照表操課。
買了一堆初學者必聽的古典音樂後,慢慢地也有了些自己的想法。
不管是大編制、小編制的器樂曲,聽不懂也就會嫌吵。而鋼琴呢?是我當時最痛恨的樂器。
這種恨法有其聲響上和心理上的理由。在聲響上,鋼琴聲對一個不熟悉的人來說,像是一連串的嘲弄、轟炸。而在心理上的干擾是幼時經驗,我很受不了家裡有錢的女同學彈琴時的做作樣。每當我現場聆聽鋼琴獨奏的時候,很難專心在演奏者做出的音樂上;我會不知覺地注視著鋼琴家 ─ 檢查他有沒有一雙做作的手‧‧
鋼琴這個樂器太令人迷惑了。誰不是常常見過它呢,該熟悉了?可是等它開聲,感覺卻又那麼陌生。你怎麼喜歡?
我就在想,有沒有單一把弦樂器單獨演奏,禁止其他樂器插科打諢?
有的,我得到了 Bach。這真是個奇妙的恩典。
「一個音響人如何聽見心裡的聲音?」
Bach 的無伴奏大小提琴組曲是我最初的喜悅,因為在這些曲子中我真正地融入、享受音樂的樂趣。音響人的器物觀反而在這兒退讓了。
「我想要這種音樂!」我開始蒐羅不同演奏家的唱片,開始會對演奏家挑剔、指指點點。
這段 AR 3a 和 LS 3/5A 並行的日子裡,我最大的收穫便是一堆的 Bach 無伴奏小提琴組曲、一堆的 Bach 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一堆的 Beethoven 小提琴協奏曲,一堆的 YoYo Ma 的錄音,和一套 Sviatoslav Richter 的大全集。
PHILIPS 的 Richter 的大全集當時對我而言是很貴的,我也不是很明白買這個全集的目的為何?畢竟是有不好的經驗麼,可雜誌的一句『獨孤求敗的偉大鋼琴家』讓我乖乖地掏出錢來。
「獨孤求敗?」真替他難過,他多想輸一次啊‧‧
這套大全集可真有大功用,它把我帶到鋼琴獨奏的世界裡,而開場的是 Beethoven 的《熱情》。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熱情》更好,我準備每天聽它」─ 列寧
年輕時的習慣是:每遇到一個新的曲目便先找些能上手的攻克資料研讀一番。
這 Beethoven 的《熱情》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啊,鋼琴家碰碰碰碰地敲擊。似乎,耐心些劈開一條長隧道,彼端陽光煦煦,一個瑰麗的世界便在你眼前。
PHILIPS 大全集裡的垂老 Richter 彈《熱情》並不適合為初探此曲的入門;Richter 中年時初訪美國時留下的錄音最是熱力四射,儘管他本人並不怎麼滿意自己的表現‧‧
《熱情》哪,像一把火,燒得我既投入鋼琴獨奏的曼妙世界,也加入蒐集 Richter 錄音的行列。
這個時候我學會了購買二手音響,好多二手銘器進出我家如「走竈腳」般恣意,印象較深的像有:
Mcintosh MC 275 新版、Klimo KENT、Mark Levinson前級、Mcintosh 75 Mono‧‧等等不勝枚舉。
那是個二手音響沒現在這麼貴,店老頭良心也還未泯滅的年代。這些短暫陣亡的銘器沒一件是我使盡潛力的,說來慚愧,我這僅兩分滿水的瓶子竟也敢在發燒友間晃個不停-大談銘器優劣。
那段廝殺時期的最後戰利品是 Esti 王盤,總算讓我知道 CD 訊源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