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待命中…

代理產品、銘器、聆聽者的劍
文章待命中…

文章待命中…

歐洲內陸的渾沌原力
源自匈牙利的 Heed Audio 不管在產品外型或者行銷方式上都相當低調,但他們的擴大機目前在歐洲已經很有名了,事實上,Heed Audio 在法國與 Rega 具有相同的市佔率。
創辦人若特·胡斯提(Zsolt Huszti)的音響之路始於「鐵幕時期」的 1980 年代,身為發燒器材愛好者的他,也是從經營一家小小的地方店鋪開始,初期主要展示Linn、Rega、KEF 和其他英國品牌的音響系統。受到鐵幕時期的律法限制,這些東西無法直接進口到匈牙利,於是他便和住在德國的哥哥阿帕·胡斯提(Alpar Huszti) 共同為當地的發燒友們建立了一種當時的代購模式——弟弟在鐵幕內招攬生意,再由鐵幕外的哥哥以旅遊的名義邀請買家到德國提貨。
1989年之後國家律令發生改變,胡斯提調整了他的業務模式,成為一個普通的分銷商和零售商,但法律的改變也帶來了匈牙利以前不存在的稅賦。在1991年,胡斯提拜訪了傳奇設計師海毅(Richard Hay,曾任職Radford,後來創辦Nytech、Ion system,還與成立了Naim的 Julian Vereker,Linn的 Ivor Tiefenbrun以及Meridian的 Bob Stuart一起組織了主動式喇叭標準協會),由於高昂的稅金,他們達成了在匈牙利裝配Ion Obelisk擴大機,但是以Heed Audio為品牌銷售的協議,至此胡斯提成為了一名製造商。之後,他也開始設計和製造揚聲器,除了擴大機賣得不錯,喇叭的部分甚至創下了每年1,500對的銷售記錄。
不過成功的喜悅並未持續下去。1992年,匈牙利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通貨膨脹率達到60%,也導致了 Heed Audio 的關閉。這段期間胡斯提前往英國拜會海毅以及TDL的創始人賴特(John Wright),後者立即向他提供了一個工作機會,不料卻在他回國準備時,賴特竟因病過世,使得計劃告吹,不得不改變職業方向。於是,胡斯提在朋友建議下自行編輯出版了一本Hi-Fi音響雜誌《Hang & Technika》,他在雜誌上刊登DIY揚聲器和擴大機的文章,讓讀者能夠使用在匈牙利市場上可以獲得的零件來自製音響設備。

傳統的繼承與權力轉移
若特·胡斯提於1993年推出了由他設計的第一款產品,一組擁有獨特電路拓撲,以橋接模式運作的前後級擴大機,算是從這裡開啟了往後30年的道路。
“Heed”這個字的發音,放在匈牙利語中代表著「橋樑」,加上過往對於胡斯提兄弟影響最深的幾個品牌——Ion、Naim、Rega、Epos、Linn——幾乎都由四個字母組成,”Heed”既包含了內在的意義,又在形式上向英倫音響品牌致敬。大不列顛的DNA沁入在Heed Audio 之中,這使得他們的產品兼具匈牙利風格和英國品牌特色,展現出一種獨特的美學。有趣的是,當海毅結束了他在英國的Ion System事業後,反倒加入Heed Audio,並成為他們在英國的分銷商。
千禧年間,Heed Audio 應Rega匈牙利代理商的要求開始生產適合當地電網架構的電源供應器,並逐步擴展到唱頭放大器和耳擴。後來,一位德國的代理商由於對他們在80年代和90年代製造的Obelisk緊致型擴大機(鞋盒般的尺寸)印象深刻,提出重新生產的希望,卻沒想到竟遭到胡斯提拒絕,因為那過於困難、昂貴而且只會帶來太多的麻煩,他決定永遠不再涉及高端擴大機的製造。

保守中的大膽調和
正如歷史所顯示的,這位德國代理商還是說服了他,但最終交付的擴大機是由一位年輕且才華橫溢的匈牙利電子設計師阿提拉·奧拉(Attila Oláh)全面改進的版本。
奧拉念大學時曾經受雇到Heed Audio當設備與庫存物品的「搬運工」,正在攻讀電子學的他對胡斯提的工作感興趣,並在查看Obelisk的線路原理圖後,指出可以改進的方法。於是他便從臨時工、兼職員工一路幹到正職的電子工程師,現在不僅負責Heed所有產品的電子設計,還成為了公司的股東。胡斯提則負責基礎設計、外觀和生產製造,以及協助奧拉進行最終調整。
雖然阿提拉·奧拉是一位相對年輕的電子設計師,但他在電路設計方面保持著一些傳統手法,他使用所謂的Transcap(調諧式非直接耦合)拓撲結構,非常類似於真空管放大器電路。在大多數擴大機製造商都採用直流耦合的時代,使用電容耦合電路變得很不尋常。奧拉曾表示:「大家選擇使用直流耦合是因為電容耦合會導致功率輸出稍低,而帳面上的失真數字偏高,但他們忘記了電容耦合聽起來聲音更好。功率放大器需要驅動揚聲器,而揚聲器(特性)喜歡電容耦合,不是直流耦合。我們還使用標準的PNP/NPN雙極輸出,這種方式看起來非常像真空管機的輸出級。」也正是如此般的電路設計,使得Heed Audio可能是全球唯一仍在使用這種拓撲結構的公司。
另外,公司上下裡不僅有奧拉這樣的「老派」設計師,整個生產線也保持著傳統手法,每個產品都是完全手工製造的,他們甚至不使用流體焊接槽,而是手工插入並焊接每個元件至PCB。如果拿一部具有316個元件的Lagrange擴大機做為例子,對於血統純正的歐洲製造品而言,這樣的方式確實令人印象深刻。



目前Heed Audio 的產品線有下面這幾種:
代表半尺寸(鞋盒大小)機種技術成就的 thesis 論文系列
首款標準尺寸的 lagrange 拉格朗日系列
成名代表作的 obelisk 方劍塔系列
老少咸宜的 elixir 萬靈丹系列
小體積的 modular 模組系列
體現聲響觀的 speaker喇叭系列
種類涵蓋擴大機、唱頭放大器和耳擴,以及D/A轉換器和CD播放器等,除了運用引以為豪的Transcap(調諧式非直接耦合)技術,並保持著一貫的高品質和精緻手工,對於那些追求音質和手工工藝的人來說,Heed Audio 成為了一個難以抗拒的選擇。
音樂、器材、人。我一直認為玩重播的過程中同時得兼顧到這三個面向,在這三者之中取得巧妙的平衡,才是真正的享受。然而數位流時代開啟之後,不只人(聆聽者)的面貌模糊了,音樂更加速地變成點綴,或淪為某種工具,消費者對於「聆聽音樂的三個層面」—外在感官的、內在情感的、結構理論的—也經常(只能)被從業人員引導至聲音最表層的官能性特徵。
上週六到竹北「新憩地」音響咖啡館演講時,播放了一段由華爾特(Bruno Walter)指揮哥倫比亞交響管弦樂團演奏的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命運》第一樂章,很意外地,由日本SPEC組成的套裝驅動起TAD Evolution One時,並未出現類似展覽會場上那種過度激烈的、兵戎相見的聲音,展露的是高價音響特有的質地感、權威性,保有極佳擴散性的同時卻又具備大能量與控制力的優勢,令樂曲的織度清楚呈現。
我很喜歡華爾特的指揮風格,帶有一種舊世紀的優雅、古典和傳承,不會過份主張自我,音樂在他手下往往得以現出原貌。而這張由Sony轉錄再版的貝多芬五號,雖然音質備受詬病,而且樂團水準亦有其侷限與瑕疵,但種種條件加在一起,反倒湧現出貝多芬音樂的一種原生特質—"ugly"。在第一樂章的中間,由主題變化後的齊奏進到雙簧管獨奏的段落,再繼續發展時,結構穩固,如巨浪般的能量衝了過來,彷彿聽到了貝多芬的怒吼,不斷激勵著、鼓舞著。剎時我想到了席德進。
對台灣畫壇影響深遠的席德進在四十多歲時才真正找到屬於他自己的代表性技法,然而卻在作品正處於圓融期的58歲時就因胰臟癌過世。攝影家柯錫杰曾為他留下了這幅著名的肖像照,同年八月席德進便逝世。準備拍攝這張照片時席德進身上拖著一個膽汁瓶,而且身體虛弱,一度直接倒在地上,柯錫杰在旁吼著,並殘酷地將他踹起來。蓬頭亂髮、面容枯槁,但目光如炬,簡直要照破百年黑暗似的。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席德進留下了這麼一幅的影像。

文/傑拉德
「我在自己喜歡的聲音裡浸泡了些年。」
興趣稍轉向了音樂,當時,注意的也都是與音樂有關的,諸如書籍雜誌、演奏家、演奏會、CD 店等。
1997 年 8 月 1 日 Richter 離開塵世。這一年我 30 歲,換了工作:由 0、1 世界篩金的資訊技術者轉換為人情世故堆裡做學問的業務員。我的世界從單純躍入複雜,是有些混亂需要適應。
Richter 的離去頗讓我悵然若失,這是一個微妙的情緒,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在樂友間的兩極化評價‧‧這種「與之同在」的微妙感覺很難形容,從小聽音樂學音樂的朋友可能會覺得奇怪─彷彿音樂家的故事應與音樂本身分開來?
音樂是可以獨立存在,但音樂家凋零便是凋零。他與任何一位成就不凡、對人們貢獻良多的秀異人士相同,當他們活著的時候,給我們多大的鼓舞啊。體會「與之同在」,是生活的小小甜美,也是一種激勵。
我不知不覺便跨出自己的音響象牙塔。
住處附近有一個髮廊,老闆娘頗與人為善。店裡常有一些奇人異士出沒。
有一回,我一面理髮一面與一對等待中的夫妻在聊 Beethoven 鋼琴奏鳴曲 op.106 《Hammerklavier》的終曲復格,老闆娘聽著興味盎然‧‧竟出言相求幫她們髮廊小姐們上一堂「古典音樂欣賞」課‧‧
我答應了。以一個半小時囫圇吞棗似的跑完了我所知道的,關於欣賞古典音樂的,枝枝節節。
我雖然講得不好,可,我竟已轉型成「專業愛樂者」了?!

「2002 下半年,胸中有一股聲音鼓舞我換更好的擴大機。」
Ensemble Reference silver 仍是我的絕對聲音(absolute sound)標竿。AN kit-1 聲音挺好但醜,它的外型一直傳送一個微弱的訊息「把我換掉‧‧把我換掉‧‧」;首先,我得試著摸個法子讓它升級,看看它是否有很大的潛力仍未發掘?
有的,網路上有一大堆牛鬼蛇神是靠升級 kit-1 維生的,我不敢擅自更動。來到 ROM 網站,這是我與這個網站的初次邂逅。網友們很親切地建議我回頭找黃智鈺,我對這個網站有種莫名的喜愛,成了它忠實的讀者。
黃智鈺花了很多時間解釋 kit-1 的製作哲學,淺顯易懂,頓時讓我打消了升級計劃。但麻煩的是,我竟然對他的另一個作品 Village 300B 產生了興趣‧‧純從技術觀點看來,黃,總是有辦法讓我與他一起共鳴、共舞‧‧極間變壓器 (interstage transformer)、排除交連電容,好像是咒語,我心中那該死的「極簡」種子正快速萌芽,DHSET + Full Range Driver 是個陰險的信仰。
中間也一度考慮 Ensemble 的高級綜合擴大機,但也因為價位、特性等考量而摒除了。音響論壇上柯逸郎先生的文章讓我花了一大筆錢做實驗,他提到 Lowther PM4A 和那難搞的音箱,不過他也提示了搭配 300B 這類管機是另外一個境界的聲音。
「另外一個境界的聲音」好!讓我不辭勞苦來搞它。我火速地組了個 Acousta 115a 改良V型壓縮式的背載號角音箱配著昂貴的PM4A。也火速地處理掉它們。這才恍然大悟「這類神物根本不是一個不會DIY的人該碰觸的」呀!極簡,絕對是極鳥、極其繁複思索行動淬鍊後的結果。
我龜縮地回傳統主流。一個機緣,竟讓我買到 Ensemble subwoofer ─PROFUNDO,拿來搭我的 Reference silver 正好!
代理商朋友甚至幫我找來了二手 Ensemble 稍早期金光閃閃的前後級,嗨,我從來沒料到能擁有這麼多的 Ensemble,這麼多的瑞士高檔貨。
「Don’t lose your common sense. Everything at the end of the wire is just other people」 ─ Esther Dyson
2003 年我開始在網路上瀏覽、留言。
網路真是有趣,即使只是討論音樂音響兩個題目,都可以演得像影片《英烈千秋》般壯烈。
有趣。但很費體力。
「沒有人在意什麼是愛樂者,唱片演奏家的靈魂?」說的也是,我們的靈魂在真實生活裡都很難喚回了,遑論虛擬世界?
網客們在網路上搞串連,其實像是另一型態的交友;先黨同伐異一番,下一步就是發起網友會了。我藉此也交了一些朋友,不過,我很難認同許多人去發燒友或愛樂人家中只是滿足戀物癖,主人豐富的特色卻只能寫在一張張便籤上,貼在他的 Goldmund 擴大機、B&W Signature 800,或是 Wilhelm Furtwängler 絕版的唱片上‧‧
下一次到另一個網友家時,自動便依腦海裡已歸檔的網客誌「喇叭篇」、「CD 篇」喚起某甲,脫口便出「喔!我上次在某某那兒聽到的聲音─真是難聽啊!」
來到 ROM 後,我想寫些不一樣的。
我不想填充 content,有太多人在講音響,講音樂。我想創造一種不一樣的描述方式,「說」的方式要比「故事」本身更重要些。什麼虛擬社群能有這種氛圍呢?
ROM 有!因為在當時整個網站幾乎只有我在寫。
「我們希望和大家分享的,是緣於對自己音樂的喜愛和欣賞,而延伸對音樂內容或形式感性與知性的深層了解,試圖從更廣泛而不同層次的領域切入,期待能以相當程度互動的方式,讓大家在這裡都能充分享受音樂,欣賞音樂之美。」 ─ ROM 站長
坦白說,這段開場白是陳義過高了。
但這也顯示成立一個社群初期的熱情、理想,我喜歡這個網站;特別是它的成員們與黃智鈺都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2004 年春,我終於買了 Village 300B。
某種程度上,這是設計師走了極端的產物─但它有合理的設計哲學;某種程度上,擁有它的人被迫往優質的高效率喇叭一途望去。
「單端直熱三極管機」推動高效率全音域單體組成的喇叭能到達什麼境界呢?這個命題走上了極端。
極端的問題是不可能三言兩語隨意應付便可成事。
這是設計師認為的極簡。什麼東西都是簡簡單單地,可以發出純而又純的直接美音。我以為,極簡這命題的條件相當複雜,首先,高效率喇叭頻率響應要稍優異就得做大,又要配合著良好的聲學條件─即意謂聆聽空間不能小;再則,高效率喇叭會暴露機器所有設計不足處,這,有很大程度是要整治電源─機器的靠師傅,牆上的靠自己。
能不能不整治,而仍得極簡之優處?
可以。極簡可分二類,物質上的極簡,和精神上的極簡。如果你啥都不處理,那定是如傑拉德一般,取後者。
可這精神上的極簡與心靈上的極簡又極是不同,畢竟還是落在玩物的軌道上。

「第二十四變奏 Fughetta 小賦格曲,同時具有冷酷及熱情的兩面性格,自然而不做作,充滿了嚴肅、安慰及愛的流露。」 ─ Jürgen Uhde 評貝多芬《狄亞貝里變奏曲》
貝多芬晚年用了大量的變奏與賦格,寫作技法繁複多變,但聽覺上並不艱難。難的只是聆聽者願不願意敞開自己,讓貝多芬衝破印象中固有的古典框架。我最著迷他的作品 op.106、op.120,每一次聆聽都有智趣的滿足感,這真是一個平衡物欲的好法子。
2005 年,這是我的 Années De Pèlerinage 的最後一年 ─ 在法國。
像是自己的變奏與賦格,
我從傳統錐盆 JMR Offrande 換至全音域 Supravox,
再由傳統錐盆 JMR Concorde 換至全音域 PHY-HP。
JMR 的喇叭是我所激賞的設計,我認為它們的音色已經很『接近』現場演奏的樂器質感,但是仍舊不夠輕鬆。每個喇叭設計者都想讓聲音逼近現場,可惜的是,每一對認真製作的喇叭都只能拾取現場音樂的某些面向。有些抓住了樂器的形體,有些能表現寬鬆自然的搖擺感,有些是對的音色,但沒有萬能的 silver bullet。
最終還是回到單端直熱三極管和全音域的「極簡」世界。
這是一種妥協嗎?
「你的錢包打開讓我看看,這樣我就可以了解你的思想與思考模式。」 ─ 邱永漢《如何成為有錢人》
單端直熱三極管和全音域的「極簡」組合是一種妥協嗎?是的。
一切都是空間的因素。
我的聆聽空間不怎理想,喇叭必須放在寬邊;我又希望聲音能儘可能寬鬆自然,所以落地型的喇叭是我挑選的對象。這樣一來,聆聽方式便成了近場聆聽─離喇叭非常近,近到傳統多音路喇叭的低音盆直接將聲音打到我身上‧‧‧JMR Concorde 就是這個因素不得不被請出門,它需要更大更大的空間。
我有能力買喇叭,但無能力換空間。我的思考模式一如我乾癟的錢包,始終只能是個荒唐的音響人,而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 audiophile。
我的新歡是個沒有分音器的12吋同軸單體,組合在一個輕薄、底部是空的音箱裡。音樂一放,整個箱體都在振動。
我很喜歡這種 Vibrant 的聲音。雖然對某些音樂來說它振動過多,但絕不是難聽、或是贅語不休的聲音;是一種不識趣的頑皮,並不影響音樂主體的聆賞。
應該是終點了。
我不禁喃喃自語,音響該重現原音嗎?每個音響人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認為『音響藝道並不只為重現現場音樂而生』,頂多,那只是個流派而已。
音響工藝為什麼不能只靜靜地擺在那兒,凝視它的人自有樂音自心中來?
《Stereo Sound》是一本我很崇敬的音響雜誌,他們很專業地在構築一個音響之夢。一幅幅美麗的器材照片,讓我的戀物欲都昇華了起來。你若問我「想不想立即擁有 FM 、47 Lab、Goldmund,Viola?」我不會想。
會那麼想的人一定有個深不見底的錢包,還有一個遠大的夢想,我沒有。
我有自己喜歡的聲音。

文/傑拉德
「1995 年是個重要的時間點。」
我換了 Apogee 的鋁帶屏風喇叭,以 JADIS Defy-7 推動。
那樣輕鬆自然的聲響,是我不曾體會的,我開始嘗試買一些交響樂的 CD 來聽。
Apogee 沒有很強很過癮的音壓,但是它像四面八方撲來的音粒,一般錐盆喇叭很難做的出來這種效果。鋼琴和提琴的形體感很足,但高音細節再生就不那麼令人滿意。弦樂器擦弦質感尚無法真實呈現。
大編制大音壓下,Apogee 的鋁帶會拍邊。這顯示某些頻段阻抗陡降,JADIS 並無法有效驅動。
JADIS 在我年少歲月中一直是超高級品牌的象徵,Defy-7 用的是 KT88 管子,這也是我與這個牌子這種管子的最後邂逅。
JADIS 推不動,那就換 Boulder 250 AE 兩台上陣。Boulder 還真厲害,直到出脫前它還未讓Apogee 拍邊呢 !只是它沒味道,聽它唱歌,總像是用一流的白水煮一流的白麵─健康但不好吃。
我終於還是忍不住換掉它們:Esti 王盤 → JADIS Pre → Boulder Power → Apogee。接下來有趣了,該換什麼呢?
那一陣子工作的很沒有滋味,直想離開台灣赴 buenos aires 依親另起爐灶。音響自不能少,可是這回得費些心思挑套小一些、易裝箱運送的器材囉,所以我暗自做了個決定:高品質 CD Player → 高品質綜合擴大機 → 超高級書架喇叭 便是我此趟重點。
我約略記得雜誌上有評過 Ensemble Reference Silver 喇叭,盛讚它的高貴質感。依此方向尋家店頭試聽,一聽之下,我整個人都傻在當場─這不是真實的音樂啊,這是人造的世界‧‧可是它聲音好美好美‧‧這是我面對音響器材唯一感動的一次。
就像我在音樂廳裡只被聖馬丁室內樂的莫札特《Eine Kliein Nachmusik》感動流淚過那麼一次一樣,再要感動容易,流淚則萬萬沒有辦法哩,這應該就是經濟學所云「邊際效應遞減」之故。
我買了這喇叭加腳架,還有同廠的綜擴 T50 前管後晶混血機。接下來是訊源了。
蠻幸運地,Micromega Duo 2.1 + Duo Pro 便進我家門,這組合讓我愛不釋手,幾乎每天都花四、五個小時聽音樂。聽到後來,索幸哪兒也不去了,就留在這孤島上當快活的音響客。
這段時間裡,我由 Richter 大全集中延伸了一些曲目。
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是 Schubert 的鋼琴作品,我幾乎在無導聆資料輔助下獨自開創了屬於自己的
曲目。
這個過程讓我信心大增,讓我相信自己也可以同時是個愛樂者。
由音響客到愛樂者,我欣喜若狂。
「一種微形非主流音響工業型態,傾盡所知所能,精益求精,只為自己與少數知音而存在。」 ─ 黃智鈺
1996 年我換了住所,Ensemble T-50 似已不敷使用。
我在街頭上閒逛─等待果陀,終於遇到一家挺有個性的音響工作室。
初識黃智鈺。他是前〈音樂與音響〉雜誌的主編,你知道的,這等頭銜對我這雅好門面的焚琴煮鶴之徒而言,煞是嚇人哩。這店有個數學味兒很重的名字「拓樸」,Topology 正是我這唸純數學的,多年前的舊學呀。
Audio Note kit-1、300B,醜陋的機器,尚能接受的售價,我坐下來不到一個小時便暗自決定要擁有它。7 W,推 Ensemble Reference silver 竟可以有飽滿不失纖細的聲音。
我發現一件趣事:一個音響店可以不擺銘器,可以不發出任何好聲音,聆聽環境可以不舒適;只要憑藉設計者的熱血理念,還是能夠成就買賣。幸運的是,我不必為了支持他人的理念而犧牲自己的原則,kit-1 還真他媽的好聽!
至於「單端直熱小功率三極管擴大機」、「全音域喇叭」這樣的音響美學種子尚未在我心中萌芽。總之,知道是有這麼一撮人幹這麼一檔事就是了。
1996 ~ 2002 年,我不曾再換過一件音響器材、交過一個音響朋友、看過一本音響雜誌。

文/傑拉德
熱心音響的人很自然地會蒐集屬於自己的音樂。可能,這些音樂的數量不大;也可能,遭致某些愛樂者物議。
我是想得開,承認自己喜歡的是聲音,並沒有什麼難為情的。我喜歡良好音響播放出來的「聲音」,想像它、幫它編個故事,相信這樂趣並不下於聽「音樂」。有時候我還覺得,我的想像力比單純的愛樂者更好呢,當這些神妙的時刻來臨時,我想,我聽到的應該就是音樂家的私語了。
回想起自己一路以新台幣與音響獸拼搏過來,除了一身血、滿口胡說八道的音響經之外,對聲音的深一層認識應是最大收穫。容我試著簡單地將這荒唐寫下。
「AR 3a」
1994 年發生的事。一個很好的同學自遠地來,要我陪他按圖索驥,尋新千里馬 AR 3a 去。
乖乖,我一聽到 AR 3a 播放的鋼琴聲,二話不說立刻墊了一個多月的窮薪資進去‧‧‧
那便開始了我無止盡的音響玩物興。
當時身邊只有一部 6L6 Push-Pull 管機和一組喇叭線,我每天下班後都把時間全耗在 3/5 A 與 AR 3a 喇叭線更換、擺位移動之間。
AR 3a 似乎從來都沒有發出真正驚豔的聲音,糊糊的自前方兩米處不住地丟音樂糊塊給我,可當時我竟沒有能力去改善它。
一天,一個同學來我家,試放了一張很難聽的 CD,鋼琴家 Richter 彈奏的舒伯特。那是一種很開玩笑的錄音水平,坦白說,我當時很不以為然這類歷史現場記錄,「可能只是給在乎音樂的人聽的吧?」我心下暗自嘀咕「 癡人。」
我有點不高興,話裡帶刺地責問他「為什麼要花錢在這種料上頭?」把鋼琴家、錄音兩損哩。我那羞赧內向的同學顯然很不好意思,整個晚上都在試圖解釋他也是依專業音樂雜誌評鑑購買的啊。
這個 Richter 頗讓我對同學的品味起了疑問。
「我在 AR 3a 上停留了一段長時間。」
一來確是因為阮囊羞澀,再來也因為花了一些心思在音樂軟體上。
「音響是手段,音樂才是目的」這句銘言,現在是頗不以為然,但在當時卻不敢不奉為圭臬。我買了幾本介紹古典音樂的導聆書、CD 指南,就此按圖索驥、照表操課。
買了一堆初學者必聽的古典音樂後,慢慢地也有了些自己的想法。
不管是大編制、小編制的器樂曲,聽不懂也就會嫌吵。而鋼琴呢?是我當時最痛恨的樂器。
這種恨法有其聲響上和心理上的理由。在聲響上,鋼琴聲對一個不熟悉的人來說,像是一連串的嘲弄、轟炸。而在心理上的干擾是幼時經驗,我很受不了家裡有錢的女同學彈琴時的做作樣。每當我現場聆聽鋼琴獨奏的時候,很難專心在演奏者做出的音樂上;我會不知覺地注視著鋼琴家 ─ 檢查他有沒有一雙做作的手‧‧
鋼琴這個樂器太令人迷惑了。誰不是常常見過它呢,該熟悉了?可是等它開聲,感覺卻又那麼陌生。你怎麼喜歡?
我就在想,有沒有單一把弦樂器單獨演奏,禁止其他樂器插科打諢?
有的,我得到了 Bach。這真是個奇妙的恩典。
「一個音響人如何聽見心裡的聲音?」
Bach 的無伴奏大小提琴組曲是我最初的喜悅,因為在這些曲子中我真正地融入、享受音樂的樂趣。音響人的器物觀反而在這兒退讓了。
「我想要這種音樂!」我開始蒐羅不同演奏家的唱片,開始會對演奏家挑剔、指指點點。
這段 AR 3a 和 LS 3/5A 並行的日子裡,我最大的收穫便是一堆的 Bach 無伴奏小提琴組曲、一堆的 Bach 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一堆的 Beethoven 小提琴協奏曲,一堆的 YoYo Ma 的錄音,和一套 Sviatoslav Richter 的大全集。
PHILIPS 的 Richter 的大全集當時對我而言是很貴的,我也不是很明白買這個全集的目的為何?畢竟是有不好的經驗麼,可雜誌的一句『獨孤求敗的偉大鋼琴家』讓我乖乖地掏出錢來。
「獨孤求敗?」真替他難過,他多想輸一次啊‧‧
這套大全集可真有大功用,它把我帶到鋼琴獨奏的世界裡,而開場的是 Beethoven 的《熱情》。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熱情》更好,我準備每天聽它」─ 列寧
年輕時的習慣是:每遇到一個新的曲目便先找些能上手的攻克資料研讀一番。
這 Beethoven 的《熱情》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啊,鋼琴家碰碰碰碰地敲擊。似乎,耐心些劈開一條長隧道,彼端陽光煦煦,一個瑰麗的世界便在你眼前。
PHILIPS 大全集裡的垂老 Richter 彈《熱情》並不適合為初探此曲的入門;Richter 中年時初訪美國時留下的錄音最是熱力四射,儘管他本人並不怎麼滿意自己的表現‧‧
《熱情》哪,像一把火,燒得我既投入鋼琴獨奏的曼妙世界,也加入蒐集 Richter 錄音的行列。
這個時候我學會了購買二手音響,好多二手銘器進出我家如「走竈腳」般恣意,印象較深的像有:
Mcintosh MC 275 新版、Klimo KENT、Mark Levinson前級、Mcintosh 75 Mono‧‧等等不勝枚舉。
那是個二手音響沒現在這麼貴,店老頭良心也還未泯滅的年代。這些短暫陣亡的銘器沒一件是我使盡潛力的,說來慚愧,我這僅兩分滿水的瓶子竟也敢在發燒友間晃個不停-大談銘器優劣。
那段廝殺時期的最後戰利品是 Esti 王盤,總算讓我知道 CD 訊源是非常重要的。

說到參觀音響展,其實參展、觀展,根本上是兩碼子事。08年四月,在高雄國賓飯店,楚培首次「參展」,感覺像平常被寵壞的老饕,主客互換首次下廚,異常緊張;同年八月,地點變成台北圓山飯店,這次則是拿著剛到手不久的新材料下鍋,主要在看新料理的可塑性與客人們對它的反應,廚藝大概不是重點。在那兩次的展覽裡,我只擔當調音工作,而本次展覽從頭到尾自行規劃、運送、佈置,所以,待我想到文宣品以及佈置品都還沒準備妥當時,已是開演前幾天。怎麼辦?就硬著頭皮上吧,我想。
「乾脆甩開商業展覽的考量吧。」顧不得包裝與形象的話,那就勇敢秀出自己,其他的交給老天爺了。於是,品牌、燈光、招待人員等細項都不管了,就把核心放在「聲與樂」(Sound & Music)這樣的主軸上,以能夠顯現器材本身價值、首都音響價值、楚培樂坊價值的器材搭配和展房佈置方式,貫徹我的意志。正因如此緣故,我做出不得已的、峰迴路轉的、柳暗花明的決定,就是將店裡的配置、擺設以及內涵,盡可能地移植到展房。
「高雄國際Hi-End音響大展」,這個Hi-End(High End,高到頂了!)所指向的是某種極致,也許是內在的、精神的、意志方面的極致,也許是物質的、外觀的、表象的極致,總之,就是一種激勵著大家往上走的訴求。另外一條路則是,若有辦法以極簡的搭配造就出極豐富的聲音,我認為這也是一種Hi-End。
音樂與音響的欣賞,本來就存在著許多不同的面相。撇開現場音樂演奏不談,透過音響器材聆聽音樂時,除欣賞音樂本身的美好外,同時也欣賞著因系統自身的特點所造就出屬於個別的音色,而融入在樂音當中的「聲響」。拿巴哈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第一號,G大調的第一樂章《Prelude》(Cello Suites No. 1 in G major,BWV 1007)來說吧,就音樂欣賞的基本面相,首先,G大調代表著光明,演奏勢必不能偏向鬱暗,速度是否符合Prelude(前奏曲)的規範,之後,再深入聆聽演奏者運弓時的控制技巧,對於樂句、呼吸的處理方式,再逐步進展到音色的呈現、變化,個人意念和音樂內涵的體現程度,以及對於原曲的詮釋及演繹是否符合時代精神等等。換到欣賞音響系統的基本面相時,播放同一首曲子,不同的系統不同的組合搭配,如台式的、美式的、日式的、義式的、英式的、德式的,一樣的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透過各式系統出來,會呈現出許多不同樣貌的聲音表現,德式的直、台式的鬆、英式的鬱、義式的濃郁、日式的精細、美式的大氣,只要更換器材、改變搭配,便能品嘗因品牌、地域、人種、技術與文化背景所造就出對於「聲響」的認知差異,而帶來含於相同樂音中的不同風味(當然,這邊並未把品牌形象所帶來的效應列入考慮的面相選擇之中)。
「就是要活起來,要讓系統發出活生生的音樂!」,這是我面對音樂與音響時不變的態度。基於此,楚培樂坊並不拘泥於挑選哪些器材,甚至,品牌強度也只是其次,重點是能否找出合適的東西並加以整合,使整個系統發出有魅力的聲音,讓音樂跳舞。這一次的展出,是個昭告的開始,除了清楚表達楚培樂坊在音樂與音響的欣賞面向外,亦體現了我們對於Hi-End的定義。
喇叭部份,選的是法國JMR Emeraude(綠寶石),雙倍磁鐵、雙層音圈二音路傳輸式落地型揚聲器;器材部份,擴大機是法國Atoll IN100,100w綜合擴大機。訊源則分為兩種,一是丹麥Holfi Xenia,16bit 44.1khz CD Player,一是法國HD micromega WM-10數位流無線傳輸播放器。
至於導線的部份,除了喇叭線之外,其他的連結都採用楚培樂坊的產品:
電源線為EVERYTHING系列,Xenia CD PLAYER的訊號線為「荊璞」,WM-10無線播放器的訊號線為採接單訂製的「盤古」。硬體搭配就在精心考量並不斷反覆測試下確立了,這就是之後所有人在會場看到、聽到的設置。
「意志的世界唯有透過表象才能體現一切。」
這是我說的,翻成白話大概就是:縱使你在心理建構了一座無與倫比的雄偉宮殿,也都還是假的,讓大家可以接觸到這座宮殿才是真的。我想讓更多人聽到「高度傳真」的聲音,我想讓更多人聽到有氣質,能夠享受愉悅的聲音,我想讓更多人聽到在有限的預算內,經過良好搭配的系統所能發出某種極致的聲音;為了完成這些計畫,除了靠硬體,當然,軟體的挑選也非常重要。
展場不同於平時,播放音樂,必須在短短幾秒內抓住聽聽眾的耳朵。人耳內有兩萬多條神經,但並非每個人的神經都具備相同的敏感度;不過即使如此,如同視覺、嗅覺般,人耳在聽覺方面,對於某些特定音色一樣能較容易地激起共鳴,簡單地說就是:「所謂好聽的聲音,存在著普遍共通性」。而我們音響從業人員的工作便是找出具有普遍共通性的好聲音,並把它精緻化後再放大,讓「好」的特質更顯耀。

好比演出者為音樂會準備合適的曲目,其實挑選並播放好的軟體(或說好的錄音),也是讓系統能發出好聲音的關鍵之一。雖然為了硬體的規劃已耗費許多時間與精神,可過程中也無時無刻同時思考著音樂方面的問題。我先憑直覺選出50張片子,再揣摩觀展人的角度來聆聽,經過一番思維、審視,最後去蕪存菁地保留大概20張CD,內容橫跨東西,涵蓋音樂史400年,從歐洲古樂、古典樂、非洲民族樂、歐美爵士樂、通俗樂,直到華語流行樂(其中有幾張是向樂友借來的,這裡要跟你們說聲謝謝),總之,就是楚培認為具有「好聽的客觀性」特質之軟體,或者說,是經驗裡適合在會場空間播放的音樂。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些準備都做好了之後,才是真正的兵刃相接。
要在一個陌生的空間裡呈現自己熟悉的聲響有時並不容易,達到理想的狀態就更艱難,每一次的展覽都像是從混亂、整合、精緻到完美的短期密集修練過程。捲尺、雷射測距儀、拍手、吶喊,訂定喇叭與空間的相對位置時,還得不停前後左右移動箱體、聆聽比較,同時也必須考量視覺上的整體感受。最後,取了一個能與房間有較和諧共振,看起來也算舒適的折中點,並把音響架排列到相對合宜的位置上,靜靜地聽了一會音樂,接下來才是真正的Tuning,那種一連串「微小改變」的調整。
演出成果如何?嗯,萬萬沒想到我們竟然能夠以總價約36萬元的系統(2010年),在現場媒體與觀眾的開放票選中力壓眾多百萬音響,獲得「最佳展房第四名」這樣的實績。但回過頭來,還是得感謝所有與會人員的支持,或許來年再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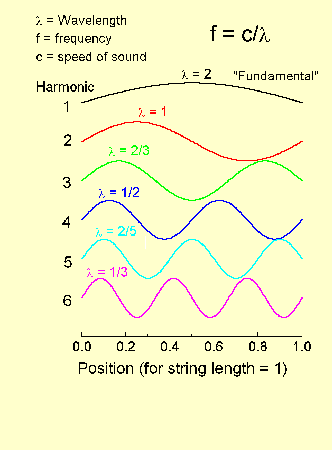
音響系統加裝超高音的目的為何?其實就是在補強泛音的「結構」,一直著重在20KHz以上基音的探討跟聆聽,不僅發現不了問題,也找不出答案。

在音響系統中,英文"Hi-Fi"所指的是High Fidelity,台灣人稱為「高傳真」,中國人則稱為「高保真」。高保真指的,乃極力保有聲音的像真度,意思應該是說:透過音響系統所發出的聲音與原音是有差距的,而且真實度一定會流失,我們只能盡力保持與真實聲音的像真度。高傳真,極力傳達聲音的像真度,感覺上想出這個詞的人,是明白透過音響,要能讓樂聲達到「原音重現」是有距離的,但是可以不斷地經由努力而趨近這個目標。
相較於「高保真」,我個人選擇具有積極面意涵的「高傳真」作為Hi-Fi的中文解釋。
先不論電子樂器的運作方式,以一般的情況來說,當聲音從喇叭發出來時,那已是對自然聲響的一種模擬,模擬出錄音(或收音)當下發聲體原有的聲音,因此,相對於原來這個「真實的聲音」,不管再怎麼模擬,透過喇叭所發出來的聲音終究是虛假的,我們只有竭盡心力地讓音響系統模擬出來的聲音,更像原來這個「真實的聲音」,才能趨近「傳真」的目的。